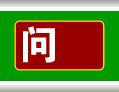用占卜、占筮或占星来占梦,都不直接从梦象出发,占出的结果虽然神秘,却不能使人在更深的层次上获得对释梦的心理满足。这些占梦术,远不如从梦象出发来释梦易于为世俗所接受。
大概至迟在春秋时,就出现了占梦书。据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下》说,齐景公一次生病躺了有十几天,夜里梦见与两个太阳格斗,自己败了。这个梦也只有古人能有,今人知道了太阳的体积、质量、表面温度,就会大可能做这样的梦了。齐景公醒来以后,越想越觉得不祥。天明晏子朝见,他就问晏子:做了这样一个梦,是不是象征着自己要死了?晏子知道景公迷信占梦,就说:“我去召占梦者来,看他怎么说。”派人用车把占梦者接来。占梦者一听,齐景公做了个与太阳格斗的梦,就说还得要翻书,晏子说:“不必翻书了。景公生的病代表阴,太阳代表阳,一阴不敌二阳,说明景公的病就要消除了。你就这么去回答他。”占梦者照晏子教的去为齐景公释梦,景公心头的阴云顿时驱散,过了三天,病就好了。在这个故事里,占梦者释梦要翻书,这书当然就是占梦书了。晏子不迷信梦书,他知道在梦书里太阳肯定是象征神圣的东西,据之解释,与两个太阳斗而不胜,肯定不是什么好兆头。景公自己疑虑重重,切不可再加重他的思想负担了。所以别立新说,借景公对占梦者的迷信,对景公进行心理治疗,果然有效。
《晏子春秋》没有提齐国的占梦者要翻的是哪一部梦书。上文提到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两本占梦书,其中《甘德长柳占梦》即使真是甘德所撰,也是战国才有的书。《黄帝长柳占梦》可能早一点,但春秋以前古代文献没有提到黄帝的,黄帝之名首见于《易经·系辞》《国语》等书,所以《黄帝长柳占梦》估计也只是春秋时代才有的。齐国占梦者要翻的,莫不就是托名黄帝的梦书?《晋书·束皙传》说:“太康二年(281),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,或言安釐王冢,得竹书数十年。”其中“《琐语》十一篇,诸国卜梦、妖怪、相书也”。《没冢琐语》收有各国卜梦的材料,却又杂记妖怪、相术,可见不是专门的梦书。这些早期的占梦书和记梦书久已佚失了。自汉魏至唐宋续有数家撰述,也大抵只能在唐以来类书和敦煌遗书中尚可窥其鳞甲。
这些梦书的体例,一般是先列梦象,后作占断;也有在梦象和占断之前,先略述释梦的根据。如:
梦见杯案,宾客到也。(《北堂书钞》卷133引《梦书》)
梦见新岁,命延长。(《北堂书钞》卷89引《梦书》)
禾稼为财用之所出。梦见禾稼,言财气生。(《艺义类聚》卷89引《梦书》)
斤斧为选士,取有材。梦得斤斧,选士来。(《太平御览》卷674引《梦书》)
在这几个例子里,梦象与占梦之间,都有着逻辑的联系。梦的含义,是直接从梦象的属性中推出来的。杯案为招待宾客之具,所以说梦见杯案,是宾客要来的喜兆。新年是喜庆节日,过一次年长一岁,所以说梦见过新年是命延长的吉兆。接下来的两例,逻辑揄的大前提都引出来了。这样的释梦,即使占梦者是在照本宣科,胶柱鼓瑟,信口开河,听的人也至少还觉得顺理成章。当然,应验不应验则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但是,同一样东西从不同的方面可以引申出不同的属性,因而对同一梦象也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,如:
梦见灶者,忧求妇嫁女。何以言之?井灶,女执信之象。(《艺文类聚》卷80引《梦书》)
灶主食。梦者得食。(《太平御览》卷186引《梦书》)
梦蜘蛛者,其日遂有喜事。(《太平御览》卷948引《梦书》)
蜘蛛为大腹,其性然也。梦见蜘蛛,忧怀妊妇人也。(同上)
这种两歧,实际上是为占梦者的圆滑应对,提供了一点回旋的余地。
梦书里有些条条不是凭常识就能从梦象中推出的,而是从历史上的梦例中演绎出来的:
梦见身上虫出,大吉。(《敦煌遗书》伯3908《新集周公解梦书》)
何以梦见身上钻出虫子为大吉?单从常识说不出道理。原来东汉明帝的贵人马氏,在永平三年春立为皇后,就在立为皇后前几天,“梦有小飞虫无数赴着身,又入皮肤中,而复飞出”(《后汉书·明德马皇后传》)。梦书中有这一条,就是从这个典故中来的。又如:
梦见上天者,大吉,生贵子。(《敦煌遗书》伯3105解梦这是从《后汉书·和熹邓皇后传》“后尝梦扪天,荡荡正青,若有钟乳状,乃仰嗽饮之”推演出来的。)
除了历史,梦书的编撰者也会从传说,自己或同时代人的梦体验中汲取素材,选择他认为占而有验的梦例总结成条。这就不可避免地犯了两个认识论的错误:第一,把本来没有因果关系的梦象和白天的遭遇,视为“梦兆”和“应验”,第二,把这纯属偶然的所谓“应验”绝对化,当作规律。例如有人夜间做梦砍竹子,第二天白天碰巧与子发生了争执,于是就总结出一条做“梦见砍竹者,主口舌”,列入梦书。拿这样的梦书法解释,又怎么会说出什么道道呢?所以,不同的梦书。往往对同一梦象有截然相反的占断。
如:
梦见煞(杀)牛,得财大喜。(《敦煌遗书》斯2222《解梦书》)
梦见煞(杀)牛、马,家破。(《敦煌遗书》伯3908《新集周公解梦书》)
梦见被刀所伤、大吉、得财。(《敦煌遗书》斯620《解梦书》)
梦见初刀伤者,失财。(伯3908)
梦见落厕者,主重病。(伯3908)
梦见陷厕污衣,得财。(《敦煌遗书》伯3281《周公解梦书》)
梦见龟鳖,得人所爱。(斯2222)
梦见龟者,口舌。(伯3908)
这些例子,都可以证明梦书中占断的随意性和欺骗性。
为了故弄玄虚,有时梦书叙述的梦象仅在规定性上稍有一些极微小的差别,占断就截然相反,如:
梦见舁棺入宅,财来。(伯3908)
梦见棺入宅,失财。(伯3908)
梦见舡泛者,忧身死。(伯3908)
梦见舡中行者。大利。(伯3908)
梦见牛马者,有大吉。(伯3908)
梦见屋中牛马、凶。(伯3908)
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梦具有模糊性,如果梦者在醒后回忆梦境,对细节分辨得不是十分清楚的话,那截然相反的占断也就在两可之间了。这种占梦,其愚弄人是显而易见的。
《关尹子·二柱篇》说:“梦中、鉴中、水中,皆有天地存焉。”单纯从这句话看,很有点反映论的味道。确实,天地之间有许多种事物,梦中就可能出现多少种事物。梦书所罗列的,毕竟是极其有限的一小部分。有许多梦,翻书根本翻不到。还有许多梦,梦象可能相当复杂,出现多种事物,或前后变幻不定,翻书也难以对号入座。这种时候,梦书就不起作用了。